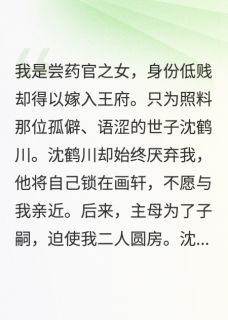我离府后,自闭世子后悔了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而备受赞誉,由小米辣辣精心打造。故事中,沈鹤川林姝惠陷入了一个充满危险和谜题的世界,必须借助自身的勇气和智慧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。沈鹤川林姝惠不仅面对着外部的敌人和考验,还要直面内心的挣扎和迷茫。通过努力与勇往直前,沈鹤川林姝惠逐渐找到了答案,并从中得到了成长和启示。”我摇摇头:”妾不知。”主母轻叹:“当年我在宫宴上第一次见到你时,你才8岁。”“那年后宫形势不稳,极其混乱,你给公主试药……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世界。
章节预览
我是尝药官之女,身份低贱却得以嫁入王府。只为照料那位孤僻、语涩的世子沈鹤川。
沈鹤川却始终厌弃我,他将自己锁在画轩,不愿与我亲近。后来,主母为了子嗣,
迫使我二人圆房。沈鹤川更加厌我,他说我脏,污了他的眼和心。再后来,他遇到一位姑娘。
她不仅出身高门,还能与他品茗鉴画,共执紫毫。就连那间我多望一眼他都要冷脸的画轩,
也任她随意出入。我知道,世子要迎娶正妻了。而我,也要离开了。
1.传闻王妃当年生沈鹤川的时候,不幸走胎。因此沈鹤川生来就与常人有些不同。
听闻他幼时就总是独坐角落,以指画地,不与其他孩童嬉戏玩耍。然而这些事,
都是在我嫁入王府之后才得知的。在这之前,
我从不知道沈鹤川对于纳我为妾这件事如此憎恶。那年洞房花烛,他掀起我的红盖头,
气到浑身发颤。“滚出去。”“这是我屋。”“滚,你给我滚!”我不知所措地垂下眼,
只恨自己不能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这满室红烛之中。第二天,给主母请安时,
她告诉我沈鹤川自幼性子孤僻,希望我理解顺从。我跪地应是。从那日起,
我便不仅要照料沈鹤川的饮食起居,还要替他熬药施针稳定心智。好在沈鹤川本性不坏,
即便仍旧寡言罕语,如今三年过去,他也渐渐能容得下我。比如施针时,他虽皱眉别过脸去,
却不再激烈挣扎或赶我。比如喝药,他不再打翻药碗,而是接过仰头灌下。还有一回,
我在外间整理药草睡着,醒来时身上竟多了一件他冬日穿的厚锦袍。但他始终不肯碰我。
沈鹤川是主母的独子,主母求嗣心切,明里暗里给我施压。可这种事,沈鹤川不愿,
我又能如何?所以如今过门三年,我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。主母终究是没了耐心,
他给沈鹤川和我下了药。我精通药理,自然知道那碗里是什么。可那又如何。
药效发作得很猛。沈鹤川呼吸滚烫,眼赤红,只剩下最原始的本能。
他毫无章法地撕扯、啃咬。像药性催出的兽,只剩蛮力。每一次冲撞都撕裂般剧痛。
我咬破嘴唇,血味混着眼泪。直至天灰白时,他僵住,瘫倒,汗浸透我里衣。不知过了多久,
身上的重量骤然消失,沈鹤川猛地翻身滚到床榻最里侧。他背对我,蜷缩,发抖。晨光刺眼,
我坐起身,发现自己浑身青紫,被褥上一片血污。2.待药效渐退,
沈鹤川的眸底逐渐从炽热转为暴怒。他猛地掀翻屋内圆桌,茶盏果盘稀里哗啦碎了一地。
紧接着是凳子、妆匣、屏风……砸完便冲出房门。他将自己锁在画轩,一天一夜不吃不喝,
任谁敲门劝说都没用。直至次日,沈鹤川才出来。他手里拿着一幅画。画里的女人未着寸缕,
身上是斑驳的青与紫。被褥上还有点点血迹。沈鹤川指着画中的女人瞪着我,
神色嫌恶至极:“脏东西。”“恶心。”“滚出去。”身后传来窸窣的笑声。
几个追来的丫鬟捂着嘴,眼睛却直往画上瞟。不远处做工的小厮亦踮脚张望,神色轻浮。
下身还在撕裂般的疼,我从未觉得如此难堪。沈鹤川将画甩到我脸上,
随后便冲出了王府大门。主母怒斥我没有照料好沈鹤川。我双腿还疼得发颤,
却也只能跟着侍卫小厮们一起去找人。可我们找遍王府四周的各个角落,却始终找不到人。
暮色四合,我绝望地瘫倒在王府门口时,沈鹤川竟然回来了。他甚至是坐着一辆马车回来的。
与他一同下车的,是一位姑娘。那姑娘气质仪态极佳,一看便知身份不凡。
她用手中的执扇挡住唇角弯弯:“今日得遇公子共赏丹青,笔底烟霞,受益良多。
”“来日画会,望还能与公子共续墨缘。”沈鹤川极为欣喜地点头。我这才知道,
原来沈鹤川是去画会了。他神游于那一幅幅方寸山水,连回府都忘记了,
是那姑娘的马车将他一同捎了回来。明明已经到了王府门口,沈鹤川却恍若未觉。
他与那姑娘谈论着今日画会上的画作,论气韵,道章法,不知日影西斜。
我不懂那些笔墨丹青,更不敢打断他们,只能默默等着。他们聊了很久很久,
沈鹤川始终没有注意到我在等他。门口侍卫是个没眼力见的:“公子,姨娘找了你一天了,
又等了你很久。”姑娘闻声一顿,回头看到我,眸光微凝:“你……已经成家了吗?
”3.沈鹤川也看到了我,面上掠过窘色。他低头踌躇半晌,终是微微颔首。
“是母亲将她……”“她是脏东西。”“很恶心。”姑娘微微一怔,
随即竟被沈鹤川那不知所措的模样逗笑了。“公子不可如此说如夫人。
”沈鹤川却着急辩驳:“是真的。”那一刻,难堪和羞愤席卷全身,
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姑娘则是微微一笑,将手中的执扇塞到沈鹤川手中,
细声道:“好啦,这个送你,我们来日再见。”沈鹤川愣愣地点了点头。
他盯着姑娘离去的马车望了很久很久。自那日起,沈鹤川更加嫌恶我。他不仅怨我弄脏了他,
还怨我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。看我一眼他都满眼厌恶。就连我给他送药,
他都是直接摔了碗。“脏,我不喝。”可林姝惠,也就是那日的姑娘,遣人送来的物件玩意,
他都视若珍宝。自那日画会的机缘,沈鹤川一直在同她互通书信。
甚至林姝惠还常来王府看他。她虽是将军府的千金,却格外精于琴棋书画。
沈鹤川把她带入他的画轩。她轻点朱砂,他勾勒远岫。他执笔示范,笔走龙蛇。她凝眸浅笑,
品评他笔下云烟。手中的药碗渐渐凉了,一股深深的倦意自心底涌起。
4.主母近来一方面对沈鹤川的开窍十分欣喜。即便贵如王府,面对手握重兵的将军府,
也不免存了结纳之心。另一方面,她对我颇为不满。“苏芷,近来你未能照料好世子。
”我垂眸,低声回道:“世子厌弃我,不愿**近,更不愿喝我熬的药。
”“那就想办法让他喝!”“王府不养闲人,世子几日未进药了?你竟还敢如此怠慢,
今日若再不能侍奉用药,仔细你的皮!”“是。”我无奈应道,心中苦涩。
今日沈鹤川仍将自己锁在画轩。眼看天色渐晚,犹豫再三,我还是推门进去了。
沈鹤川正在描摹一幅林姝惠的画像。他一见到我,眸中便满是戾气。“脏东西,滚出去!
”“谁让你进来?”“不许!”我垂直看着手中的药碗,低声说:“世子,该喝药了。
”“脏,我不喝!”话音未落,沈鹤川猛地将药碗打翻,黑褐色的药汁溅了一地。
我怔怔望着一地的药汁,终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。“真的有那么脏吗?”每日天不亮,
我就背着竹篓上山采药。回府后,我一株株挑拣,枯叶虫蛀的不要,只留最鲜嫩的。
再拿刷子一根根刷干净,用井水泡上两个时辰。在小炉上熬药时,我守着炭火摇扇子,
一熬就是三个时辰。热气熏得眼睛发酸,袖口都被熏出苦味。可药碗端到他面前只是片刻,
所有功夫都白费。我做的这一切,真的有那么脏吗?5.沈鹤川并未回应我的疑问。
他只是命人将我赶出画轩。然后命人将画轩从里到外打扫了一遍。见我还呆立在门口,
沈鹤川抄起矮凳砸在门上:“我说了,滚。”“这里是王府,是我家,不是你家。
”“你快滚!”闻言,我有些难堪地垂下头。幼时,父亲打骂,嫡母欺辱,
随时要将我跟姨娘赶出宅子。我会问:“姨娘,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家?
”姨娘总会偷偷跟我说:“以后你嫁人了,有了夫君,便有了自己的家。
”后来姨娘惨死在父亲的棍棒之下,我便再也没机会告诉她:姨娘,你错了。
6.我主动去见了主母。“妾有罪,未能照料好世子。
”“求您看在我父亲先前为王爷尝药毙命的份儿上,将妾遣归。”主母神色微变。“苏芷,
你入府三年,王府可有亏待你?”我摇头:”未曾有。”“那你为何动了离府的心思?
”“妾身自知世子厌我,如今世子与林姑娘情投意合,妾若横亘其间,徒增怨怼。
”“妾虽愚钝,亦知当退。”主母蹙眉:“你这是什么道理,男子三妻四妾本就是常理。
”“主母,林姑娘出身高门,即便面上不介意妾的存在,但面对真心相爱之人,
难免心存介怀。”“这世上没有一个女子心甘情愿跟别人共享夫君的。”主母闻言,
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:“苏芷,你可知,以你的出身,为何能进得了王府的门?
”我摇摇头:”妾不知。”主母轻叹:“当年我在宫宴上第一次见到你时,你才8岁。
”“那年后宫形势不稳,极其混乱,你给公主试药,安安静静,不哭不闹。那时,
我就看中了你。”“鹤川是我唯一的儿子,偏生上天不怜他,我自然要为他打算。
”“那林氏家中门第虽高,但到底不是个伺候人的主儿。”“什么笔墨山水,附庸风雅罢了。
在我眼中,世子的身子才是第一位的。他由你照料我才放心。
”主母顿了顿:“苏芷你知不知道,京中多少女子想要攀附王府?以你的出身,
能进的了王府的门,且这么多年世子只你一个,你还有什么不知足?”“林氏家世再好,
男人三妻四妾的常理也不是她能更改的。”主母的意思,我不是不明白。可王府门第再高,
我也未曾想要攀附。明明我只是被选中罢了。
我不甘愿放弃:“可如今世子见了我就暴怒发病,实在不利于他调养身子。眼下,
他跟心上人在一起才能稳定住病情。”“如今世子的情况愈发不好,还是不要见我为好。
”“况且,世子的病,御医什么的都能照看。其他饮食起居,丫鬟嬷嬷也能照应。
不必非由我照料。”说着我从袖子里掏出一纸方子:“主母,这是我尝遍百草配的方子,
并且亲自试了不下百次。有这方子,您可安心。”主母接过方子,没有说话。她闭了闭眼,
眼睫微颤,半晌,还是松了口。“你且先退下吧,我需从长计议。”我离开堂屋的时候,
院中竟然飘起了小雪。沈鹤川披了件墨色大氅,独自站在雪中。雪落在他肩上,
积了厚厚的一层,他也不拂。他看见我,眼眶微红:“你,要去哪?”6.“妾想归乡。
”我答道。沈鹤川没再说话,只是垂下眼,攥紧衣袍。“那你还会回来吗?
”我摇头:”不会。”沈鹤川又不说话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再次开口:“那儿是你的家?
”我一怔。我想去的,其实是我姨娘的家乡。我并未在那儿生活过,只是以前常听姨娘提起。
她说那儿有很多珍稀药材、民间偏方,市井间医馆林立。在那个地方,村老皆通《本草》,
童子亦识药性。从前姨娘常说,得空一定要带我回去一趟。如今虽天不遂人愿,
我亦想带着她的骨灰回去。见我不说话,沈鹤川突然紧紧按住我的肩膀,神色急切:“不,
不许。”我愣了愣,未曾料到他会这样说。“世子为何不许?”我问他。“你走了,没有药。
”我心中讶异:”可你从不喝。”“我喝。”我叹了口气,
缓声开口:“药的方子我已经留给主母了,以后你娶了林**,她亦会遣人熬给你喝的。
”“不,你熬。”“……”“姝惠要作画,要看书,要抚琴,她没空。
”沈鹤川竟然一连串说了这么长的句子。“你有。”我抬头望着沈鹤川急切的眼神。
落雪染上他的眉梢,我却冷得打了个哆嗦。而后几日,我熬的药,沈鹤川都乖乖喝下。
期间甚至主动同我搭话。“你,不走。”我也曾委婉地劝过他。可他性子执拗,
一句也不肯听。只是一遍遍地重复”不许走,不许走”。见我还想劝他,
他甚至开始大喊大叫:“不许走!我是你夫君,你是我的。”成婚三年,
我还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”夫君”这个词。我知道多说无益,若是他持续这样激动,
发了病,主母便更不会允我离府。于是我闭了嘴。只静静等着主母的裁夺。
沈鹤川见我不再劝他,以为我终于想通了,眉心渐渐舒展开来。
他甚至又欣喜地邀林姝惠来吟诗作画。仿佛已经笃定我不会走。林姝惠甚至还带来了她的琴。
画轩内古琴声悠悠荡开,时而清越,时而缠绵。沈鹤川的笑声混在琴音里,笨拙却真切,
像是从未如此开心。我端着药碗在廊下站了很久,直到雪落满肩头。不知过了多久,
画轩的门终于”吱呀”一声开了。沈鹤川和林姝惠一同走了出来。
沈鹤川脸上带着一种纯粹而明亮的笑意,他微微侧着身子,
下意识地替林姝惠挡住了些许风雪。他仰头望了一眼鹅毛般密密实实的雪,
忽然拉住了林姝惠的手腕。“雪大,冷,留下。”林姝惠微微一怔,
而后浅笑出声:“那我睡那儿啊?”沈鹤川不知何时看见的我,
他伸手往我的方向指了指:“你睡她屋。”我跟林姝惠几乎是同时瞪大了眼睛。“傻瓜,
为何让我睡她的屋?”林姝惠微不可察地撇了撇嘴。“她屋有炭火,其他屋没有。
”沈鹤川神色认真。林姝惠侧头瞥了我一眼:“那你得先问问你家如夫人是否同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