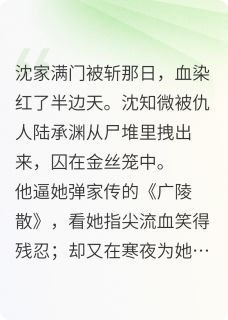他替我挡刀时,我才知他爱疯了这本小说超级超级好看,小说主人公是沈知微陆承渊谢景行,作者是全名啦文笔超好,构思超好,人物超好,背景以及所有细节都超好!小说精彩节选满门抄斩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能活着,全凭我一句话。别总摆出这副样子,惹我不高兴,对你没好处。""通敌叛国?"沈知微笑了,笑得……
章节预览
沈家满门被斩那日,血染红了半边天。沈知微被仇人陆承渊从尸堆里拽出来,囚在金丝笼中。
他逼她弹家传的《广陵散》,看她指尖流血笑得残忍;却又在寒夜为她掖被角,
在她病时守到天明。青梅竹马的谢景行拄着断腿来救她,她却笑着说:“陆承渊待我,
比父兄好百倍。”她把他的真心踩碎,只为护他周全。
直到那封揭露真相的信落在眼前——父亲的罪证是伪造的,兄长的战死藏着阴谋,
而陆承渊的恨里,早缠上了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深情。当三皇子的剑刺来,
陆承渊替她挡下的那一刻,沈知微才懂:她恨了半生的人,
爱了她整整三年;她伤了全心护她的人,再没机会说句抱歉。海棠开了又谢,而她的爱恨,
早已成烬。1囚笼沈知微坐在窗前,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琉璃盏。盏中残茶早已凉透,
窗外的海棠开得泼泼洒洒,粉白花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,
恍惚间竟与记忆重叠——那年她十三岁,兄长沈知言为她折花,指尖的薄茧蹭过她发间,
笑说:"我们知微,要像这海棠一样,永远活得明媚。"明媚?她自嘲地弯了弯唇。
如今的她,不过是陆承渊掌中的玩物,连哭的资格都没有。"在想什么?
"低沉的嗓音自身后响起,带着惯有的慵懒,却让沈知微浑身一僵。她没有回头,
只淡淡道:"没什么。"陆承渊走至她身后,温热的呼吸拂过她颈侧。
他今日穿了件月白锦袍,墨发用玉冠束起,衬得那张脸愈发俊美无俦。可只有沈知微知道,
这副温润皮囊下,藏着怎样一颗蛇蝎心肠。"在想沈家?"他轻笑,指尖挑起她一缕发丝,
绕在指上把玩,"还是在想谢景行?"沈知微猛地转头,眼中淬着冰:"陆承渊,你放开我。
"他非但不放,反而顺势将她圈入怀中,下巴抵在她发顶,声音低得像蛊惑:"知微,
别总对我这么凶。你看,我给你带了什么?"他松开她,转身从侍女手中接过一个紫檀木盒。
打开的瞬间,流光溢彩——那是一把琵琶,琴身嵌着细碎的珍珠,弦轴是羊脂白玉,
一看便知价值连城。"这是西域进贡的暖玉琵琶,据说音色绝佳。"他将琵琶递到她面前,
"弹一曲《广陵散》给我听,嗯?"沈知微的目光落在琵琶上,指尖却冰凉。《广陵散》,
那是沈家的家传古曲,父亲曾说,此曲藏着沈家的风骨。可自从沈家满门被斩,
这曲子便成了陆承渊折磨她的工具。每次弹奏,他都要在一旁细细打量她的表情,
仿佛在欣赏一件破碎的珍宝。"我不弹。"她别过脸。陆承渊的笑意淡了些,
手指抚上她的手背。那里还留着昨日练琴时磨出的薄茧,红痕未褪。"手还疼?
"他语气似有怜惜,指尖却突然用力,捏得她骨头生疼。"陆承渊!"她痛呼出声,
挣扎着想抽回手。"弹不弹?"他逼近一步,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偏执,"知微,
别逼我用别的法子。"沈知微看着他眼中的阴鸷,心一点点沉下去。她太清楚他的手段了。
他可以前一刻对她温言软语,下一刻就将她锁在暗室,
让她在无边黑暗里听着自己的哭声发抖。她深吸一口气,接过那把暖玉琵琶。
指尖触到琴弦的刹那,竟觉得比寒冰更冷。调弦时,她的手在抖,不是因为怕疼,
而是因为屈辱。《广陵散》的调子缓缓流淌而出,起初沉郁低回,像困兽在牢笼中呜咽。
陆承渊坐在对面的软榻上,端着茶杯,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她身上,嘴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。
沈知微闭着眼,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。她想起父亲在刑场上的最后一眼,
那样绝望又不甘;想起母亲自缢前,塞给她的那半块家传玉佩,
冰凉的玉片硌得她心口生疼;想起兄长战死的消息传来时,她抱着兄长的盔甲,
哭到喉咙出血......这些画面像针一样扎进她的脑海,琴弦突然"铮"地一声断了,
尖锐的声响刺破了一室的寂静。断弦弹起,划破了她的指尖,血珠瞬间涌了出来,
滴落在洁白的琴身上,像一朵绽开的红梅。陆承渊皱眉,起身走过来,抓起她的手就要查看。
沈知微猛地甩开他,眼中是滔天的恨意:"陆承渊,你满意了?
看着我像个倡优一样在你面前弹这曲子,是不是很有趣?""知微......""你闭嘴。
"她厉声打断,声音因激动而颤抖,"你救我回来,不是为了让我活,
是为了让我看着你如何享受我沈家的一切。你让我弹《广陵散》,是为了提醒我,
我沈家的风骨,早已被你踩在脚下。"陆承渊的脸色沉了沉,却没有发怒。
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,眸色深沉得像不见底的寒潭:"是又如何?沈知微,你父亲通敌叛国,
满门抄斩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能活着,全凭我一句话。别总摆出这副样子,惹我不高兴,
对你没好处。""通敌叛国?"沈知微笑了,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,"陆承渊,
你敢对着天地起誓,我父亲的罪证不是你伪造的吗?我兄长的战死,不是你设计的吗?
"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,随即冷笑:"证据确凿,你再狡辩也无用。"沈知微看着他,
突然觉得无比疲惫。她转身走到窗边,望着墙外那片自由的天空,轻声道:"陆承渊,
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。"他在身后轻笑,语气带着笃定:"我等着。但在那之前,
你哪儿也别想去。"2故人谢景行来的那天,沈知微正在廊下喂鱼。初夏的阳光有些烈,
她撑着一把油纸伞,裙摆扫过青石板,惊起几尾锦鲤。忽闻一阵压抑的咳嗽声,她动作一顿,
那声音......太熟悉了。她猛地抬头,只见月洞门外,一个青衫男子拄着双拐,
正艰难地站在那里。他身形消瘦,脸色苍白得像纸,额上沁着薄汗,显然是走了很远的路。
是谢景行。沈知微的心脏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,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。她下意识地想躲,
脚却像被钉在原地。三年了,她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。谢景行也看到了她,
那双总是含笑的眼睛瞬间红了。他张了张嘴,
声音沙哑得厉害:"知微......"这两个字个字,像一把钝刀,
割开了她刻意封存的记忆。那年上元节,他替她挡开人群,笑着说:"知微别怕,有我在。
"那年她及笄,他送来一支白玉簪,低声说:"愿你一世无忧。"可如今,他拄着拐杖,
再没了当年鲜衣怒马的模样。而她,成了仇人之囚,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。
"谢世子大驾光临,真是稀客。"她垂下眼,声音冷得像冰,将所有情绪都藏了起来。
谢景行踉跄着往前走了几步,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,一下下敲在沈知微心上。"知微,
我......"他想说什么,却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,咳得几乎弯下腰。
沈知微攥紧了伞柄,指尖泛白。她看到他捂住嘴的帕子上,洇出一点刺目的红。
"你怎么弄成这样?"她终是没忍住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谢景行好不容易止住咳,摆了摆手,笑道:"旧伤罢了,不碍事。"他看着她,
眼神里满是疼惜,"知微,你......还好吗?"好吗?沈知微想笑。被仇人囚禁,
日日活在痛苦与仇恨里,怎么会好?可她只是淡淡道:"托陆大人的福,衣食无忧。
"谢景行的脸色更白了些。他望着她身上华贵的衣饰,再看看这亭台楼阁,
喉结滚动了一下:"他......待你好吗?""很好。"沈知微抬眼,迎上他的目光,
语气刻意放得轻佻,"陆大人对我,可是言听计从。你看这院子,这锦鲤,
都是他特意为我准备的。"她看到谢景行的眼神一点点暗下去,像燃尽的灰烬。他嘴唇翕动,
似乎想说什么,最终却只是低声道:"那就好。"沈知微别过脸,不敢再看他。
她怕再看一眼,自己精心筑起的防线就会崩塌。"谢世子若是来看热闹,现在看到了,
可以走了。"她转过身,声音冷硬,"陆大人不喜外人来府,若是被他撞见,怕是要怪罪。
"谢景行猛地抬头,眼中满是难以置信:"知微,你......你怎么能这么说?
我是来......""来看看我这个沈家余孽,是如何攀附仇人苟活的吗?
"沈知微打断他,语气带着刻意的刻薄,"谢世子若是想看,我不妨告诉你,
我现在过得很好。陆承渊比我父兄待我好百倍,至少,他不会让我流落街头。""你胡说!
"谢景行激动地往前走了一步,却因为动作太急,踉跄着差点摔倒。他扶住拐杖,
胸口剧烈起伏,"知微,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!沈家的事,我一直在查,
我一定会为你父兄**......""**?"沈知微笑了,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,
"谢景行,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!你连站都站不稳,还说什么**?当年你父亲官拜太傅,
尚且保不住我沈家,如今你成了废人,凭什么说这种大话?"她的话像淬了毒的针,
狠狠扎进谢景行的心里。他脸色煞白,嘴唇颤抖着,却说不出一个字。
沈知微看着他痛苦的模样,心也跟着疼。可她不能停,必须把他推开。陆承渊耳目众多,
若是让他知道谢景行来过,以他的性子,谢景行只会死得更惨。"谢世子,"她深吸一口气,
声音恢复了冰冷,"我与你,早已不是一路人。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从今往后,不必再来了。"她说完,转身就走,不敢回头。油纸伞从手中滑落,
掉在地上发出轻响,她也未曾停下。直到走进内院,再也看不见那抹青衫,她才扶着墙,
缓缓滑坐在地。眼泪终于汹涌而出,砸在青砖上,晕开一小片湿痕。谢景行,对不起。
若有来生,我再还你这份情。3试探陆承渊回来时,看到的就是满地狼藉。
沈知微的房门紧闭,侍女跪在门外瑟瑟发抖。他挑眉:"又怎么了?
"侍女颤声道:"回大人,**......**把暖玉琵琶砸了。"陆承渊推门而入,
果然见那把价值连城的琵琶被摔在地上,琴身断裂,珍珠散落一地。沈知微坐在窗边,
背对着他,肩膀微微耸动。他走过去,捡起一块碎玉,语气平静:"生气了?因为谢景行?
"沈知微猛地回头,眼中还带着泪痕,却倔强地瞪着他:"是又如何?""他来做什么?
""与你无关。"陆承渊轻笑一声,俯身捏住她的下巴,迫使她看着自己:"沈知微,
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是我的人,你的事,就是我的事。""放开我!"她挣扎着,
却被他捏得更紧。下巴传来的疼痛让她眼眶泛红,却死死咬着唇不肯示弱。
他看着她泛红的眼眶,眸色深了深,忽然松开手。"他给了你什么?"沈知微一愣,
随即反应过来,他定是在谢景行离开后搜查过。她心中一紧,
面上却不动声色:"什么都没有。"陆承渊走到梳妆台前,拿起一个锦盒。
那是谢景行带来的,里面是一支白玉簪——正是当年他送给她的及笄礼,
后来在沈家抄家时遗失了。"这个,不是他给的?"他打开锦盒,声音里带着一丝危险。
沈知微的心跳漏了一拍,强作镇定:"是我自己找回来的,与他无关。""是吗?
"他拿起玉簪,放在指尖把玩,"我倒是听说,谢世子为了找这支簪子,
跑遍了京城的古玩市场,甚至......不惜变卖祖产。"沈知微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她不知道谢景行竟为了一支簪子做到这个地步。"那又如何?"她别过脸,
"一支破簪子而已,他愿意折腾,与我何干?"陆承渊突然笑了,将玉簪插在她发间,
指尖轻轻拂过她的耳垂:"知微,别自欺欺人了。你若是真对他无情,
就不会把簪子藏得这么好。"他的指尖带着温度,烫得她浑身一颤。她猛地拔下玉簪,
狠狠摔在地上:"我不需要!"玉簪撞在青砖上,断成了两截。陆承渊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。
他盯着她,眼神冷得像冰:"沈知微,别挑战我的底线。""我的底线早就被你踩碎了!
"沈知微也豁出去了,"陆承渊,你杀了我父兄,灭了我沈家,把我困在这里,
难道还不够吗?非要逼死我才甘心?""逼死你?"他冷笑,"我若是想逼死你,
你活不到今天。"他顿了顿,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复杂,"知微,别总想着谢景行。
他给不了你想要的,跟着我,至少你能活着。""活着?"她看着他,眼中满是嘲讽,
"像这样行尸走肉般活着?陆承渊,你不如杀了我。"他沉默了片刻,
转身往外走:"好好反省。在你想明白之前,别出这个门。"门被关上,落了锁。
沈知微看着地上的断簪,缓缓蹲下身,将碎片一点点捡起来。指尖被划破,渗出血珠,
她却浑然不觉。谢景行,你看,我们连最后一点念想,都被陆承渊毁了。
4真相沈知微被禁足的第七天,陆承渊的书房失了火。火势不大,很快就被扑灭了。
但陆承渊最宝贝的那幅《江山图》被烧毁了一角,他大发雷霆,下令彻查。沈知微坐在窗前,
听着外面的动静,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这场火,是她让人放的。她就是要让陆承渊不得安宁。
傍晚时分,侍女匆匆跑来:"**,大人让您过去。"沈知微整理了一下衣襟,
跟着侍女走向书房。陆承渊坐在书桌后,脸色阴沉得可怕。地上跪着几个侍卫,瑟瑟发抖。
"来了?"他抬眼,目光落在她身上。"大人找我何事?"她故作平静。"书房的火,
是你放的?"沈知微挑眉:"大人凭什么认为是我?""除了你,
没人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动手脚。"他站起身,一步步走到她面前,"沈知微,你就这么恨我?
""难道不该恨吗?"她迎上他的目光,毫不畏惧,"陆承渊,我恨不得食你肉,扒你皮!
"他的眼神暗了暗,忽然抓住她的手腕,将她拖到书架前。他移开一排书,露出后面的暗格。
打开暗格,里面放着一个紫檀木匣。"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真相吗?"他打开木匣,
拿出一叠泛黄的信纸,"自己看。"沈知微疑惑地拿起信纸,展开一看,瞳孔骤然收缩。
那是陆承渊的父亲陆明远写给友人的信,字里行间,全是对沈家的怨恨。原来,
当年陆明远与沈知微的父亲沈从安同朝为官,两人本是挚友,却因一桩贪腐案反目。
沈从安举报陆明远贪赃枉法,导致陆家满门流放,陆明远病死途中。而那桩贪腐案,
根本是沈从安为了上位,故意设计陷害陆家的。沈知微的手在抖,信纸几乎要拿不住。
这......这怎么可能?父亲在她心中,一直是清正廉明的形象,怎么会做出这种事?
"现在信了吗?"陆承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带着一丝嘲讽,"你父亲不是什么好人。
我陆承渊虽然算不上君子,却也只做有仇报仇的事。"沈知微猛地抬头,
眼中满是血丝:"所以你就灭了我沈家满门?!""是。"他看着她,眼神冰冷,
"我父亲的冤屈,我要用沈家的血来洗。""那我兄长呢。"她嘶吼着,"我兄长为国捐躯,
与你无冤无仇,你为什么连他都不放过。"陆承渊的眼神闪烁了一下,
语气却依旧强硬:"他是沈家人,就该死。""你撒谎……"沈知微死死盯着他,
"我兄长战死沙场,是为国尽忠,你根本没资格动他。"他忽然别过脸,
不再看她:"信不信由你。"沈知微看着他的侧脸,心中翻涌着惊涛骇浪。
信纸被她攥得发皱,指尖的力度几乎要将那薄薄的纸页戳穿。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轰然倒塌,
那些清正廉明的记忆碎片,与信中字字泣血的控诉重叠,让她头痛欲裂。
“不可能……”她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像梦呓,
“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……他教我‘忠’‘义’二字,教我不可负国负民,
他怎么会……”陆承渊转过身,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,
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:“人总是善于伪装的。你父亲在你面前是慈父,在我面前,
却是害死我全家的刽子手。”他顿了顿,从暗格里又取出一份卷宗,“你自己看,
这是当年大理寺的密档,上面有你父亲亲笔签名的供词,还有他收受敌国贿赂的账册。
”沈知微颤抖着接过卷宗,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,如同触到烙铁。
供词上的字迹确实是父亲的,一笔一划,力透纸背,可内容却让她如坠冰窟——承认通敌,
承认构陷陆明远,承认所有罪名。“不……这是假的……”她猛地将卷宗摔在地上,
泪水汹涌而出,“是你伪造的,陆承渊,你为了让自己的杀戮变得名正言顺,
连这种手段都用上了。”陆承渊弯腰捡起卷宗,掸了掸上面的灰尘,
眼神冷得像寒冬的冰湖:“我没必要伪造。沈家倒台后,这些东西本就该公之于众,
是我压了下来,给你留了最后一丝体面。”“体面?”沈知微笑了,笑声凄厉,
在空旷的书房里回荡,“把我关在这牢笼里,日**我弹《广陵散》,
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活在仇恨里,这就是你所谓的体面?陆承渊,你根本就是想看我痛苦!
”他沉默了,许久才低声道:“是,我想看你痛苦,因为你父亲让我母亲哭瞎了眼,
让我兄长病死在流放路上,让我从云端跌入泥沼,尝尽人间疾苦。沈知微,
你以为只有你在恨吗?”他的声音陡然拔高,
眼中翻涌着压抑了十几年的恨意:“我九岁那年,眼睁睁看着官差把我娘从家里拖走,
她死死抓着门框,哭喊着我爹的名字,可你父亲就站在门外,冷眼旁观。
我兄长在流放途中染了肺痨,写信求你父亲看在往日情分上赐一副药,他却把信扔进了火里。
”“这些,你知道吗?”他一步步逼近,高大的身影投下浓重的阴影,将沈知微完全笼罩,